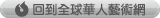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今年已64歲的Paulo Flores(保羅‧佛瑞斯),只有一頭銀白疏略的長髮顯現出歲月給予他的痕跡。高高的個子、戴著細框圓眼鏡,總是不疾不徐地汲著拖鞋出現在團隊排練場,或帶領工作坊、或講述劇場理論;當演出的時候,更是看不出他的年齡,無論戶外街頭或是室內的演出,都親自披掛上陣。作為在劇團最資深的團員、也是Òi Nóis Aqui Traveiz的創始成員之一,他以他的存在,默默地穩固著這個大膽前衛的劇團。

Paulo Flores在《米蒂亞:聲音》裡演出逼使米蒂亞離開的國王。|圖片來源:Òi Nóis Aqui Traveiz臉書頁面
在與保羅訪談時,他總是以劇團的角度發言。在公開對外的場合,他總是把自己隱身起來,希望傳達出劇團整體的理念──畢竟他們是個集體工作的團隊,不該有彰顯的階層帶領者。只有在一些不經意的時候,才會稍稍透露出他自己。
憑著一股反叛與勇氣
保羅年輕時就開始接觸劇場,當時在阿格雷港主要是阿格雷港阿利那劇團(Teatro de Arena Porto Alegre),波瓦帶領的聖保羅阿利那劇團(Teatro de Arena Sao Paulo)【1】的分支。當時很多城市都有阿利那劇團,試圖以劇場去接觸公眾,呈現劇場的政治與社會性。他因為對劇場太有興趣了,所以後來大學便念了戲劇系,畢竟那個年代不像現在,不進學院就沒辦法接觸劇場。又加上七零年代接觸了布萊希特和亞陶的理論【2】,大為著迷,後來這也成為Òi Nóis Aqui Traveiz的理論基礎。

訪談時,保羅總是就各種問題侃侃而談,我們也從白日訪至了傍晚。|攝影:黃馨儀
Òi Nóis Aqui Traveiz在1978年組團。那時候雖仍在獨裁時期,但1977年街頭運動再度盛行,也開始鼓吹釋放政治犯。當時雖然很多劇場標誌自己是左派,但做的仍是右派保守的內容,並將劇場限制在導演、演員和製作的分工階層上,因此一群年輕人覺得不滿而決定自組劇團。
儘管仍在獨裁時期,軍政府的藝文審查仍嚴格,但他們地下秘密組織劇團。因為封閉的政治氣氛,青年們難以知道外面世界的劇場做法,因此開始自己研究與實驗。像是阿拉巴爾說的:「要改變美學得先改變形式。」所以他們不斷閱讀、收集素材;但也不能只是閱讀,於是便從身體的探索開始。在那樣的時局,組團是大家一起的決定與決心,「就是一股勇氣和反叛吧!想要批判政治。」
相信美學與政治並不牴觸
因為每齣作品都有議題與主張,Òi Nóis Aqui Traveiz在當地的作品有時也會被貼上政治宣傳的標籤,但他們並不在意。「我們在意的是美學,在意我們呈現的劇場形象,以及怎麼真正地接觸觀眾?尤其在街頭。我們相信美學和政治是不牴觸的。」在創團初期,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前衛劇場等都是他們重要研究素材。而在研讀布萊希特和亞陶後,又開始接觸到葛羅托夫斯基的貧窮劇場和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尤其是波瓦的《給演員與非演員的200種遊戲》(“Games for Actors and Non-Actors”),更是他們極重要的練習材料。保羅一直沒見過波瓦,劇團目前和波瓦創立的里約被壓迫者劇場中心也沒有緊密的合作關係。兩團雖有聯繫,但Òi Nóis Aqui Traveiz並未著重在被壓迫者劇場的策略運用上,而著重在演出創作,他們以另一種方式在進行與實驗劇場對抗現實的可能。2015年製作新作品《卡利班》時,波瓦遺孀Cecília亦有參與前期工作,共同發展討論。

討論軍政獨裁時期的作品“O Amargo Santo da Purificação” ,保羅扮演主要角色、帶領反抗的知識分子Carlos Marighella(右)。|圖片來源:Òi Nóis Aqui Traveiz臉書頁面
Òi Nóis Aqui Traveiz受德國劇場影響不少,畢竟巴西的劇場發展始於歐洲的引入,但他們有意識讓其中的美學概念在地化。德國劇作家海涅穆勒給予Òi Nóis Aqui Traveiz整合布萊希特與波瓦的政治性劇場,與亞陶及葛羅托夫斯基的儀式性劇場一個可能性:藉由身體去連結政治。「表演者從工作自身開始而至工作與意識周遭社會,這樣的改變也使人政治化,並給予改變觀眾的能量。」Òi Nóis Aqui Traveiz的兩種創作脈絡也是奠定在此之上:儀式劇場創造新場域、藉由演員能量和觀眾達到另一種溝通;而政治劇場的實踐主要是在街頭,藉由街頭劇場創造移動性與觸及底層。儀式劇場和政治劇場提供他們不同的方式和觀眾對話。
以集體意識打破日常的個人化
除了劇場美學與政治的連結,Òi Nóis Aqui Traveiz實踐其烏托邦理念的另一方式是集體創作。在日常已是核心個人化與分工階層化的現代社會,到底集體創作如何可能?保羅表示,集體工作是每個成員都有的意識,他們也努力每天實踐之。尤其為了邁向不存在的烏托邦,沒有前例,只能嘗試。

帶領工作坊時的保羅。|圖片來源:Òi Nóis Aqui Traveiz臉書頁面
每一次的作品製作,都會經由團員共同討論,要做哪個作品在在反應了團員對日常的思考與反省。像是2015年在巡演時,他們便開始討論下一齣街頭演出要做什麼?《卡利班》經由雙重改編:改編自波瓦改編莎士比亞的《暴風雨》,關於拉丁美洲的受壓迫與殖民處境。1974年波瓦在阿根廷做了這齣戲,以討論拉丁美洲被剝奪的自由、民主和獨立,揭示美國的政治介入。這樣的狀況在現在依然適用。
同時他們也很開放新成員加入,但欲參與者得先了解劇團的意識形態和工作方式。這樣的理解也是種過程,在劇團的理念下工作,也會經歷自己的階段變化,不一定每個人都能接受,所以會有人來有人走。目前有20餘名成員,其中九名是核心成員,都有五年以上的參與經驗。
在街頭遊行之前,保羅再次和民眾劇場學校學生確認演出細節。|攝影:黃馨儀
用劇場打開人們的心
Òi Nóis Aqui Traveiz相信戲劇會帶來改變,而這其中的改變只有自己做的人最知道。所以即使經歷過很多困難,劇團仍勉力支持。現在也是個艱難的時刻,2015年起因為右派開始執政,政府補助大幅短少、甚可說沒有,只有一些企業文化基金會的製作經費。2016年後阿格雷港的文化局近乎名存實亡,很多團隊找不到資金、排練場地,或是能搭檔的夥伴,援助全失。
面對未來,保羅目前不敢多想,卻仍堅地的說!「這40年來,巴西多半處於封閉的狀態,我們能做的只有盡量用劇場打開人們的心。有些人也質疑我們做的劇場窮人又看不懂,但總是能觸及多少是多少。關於未來我目前還無法多想,因為現在是個艱難的時期,只能繼續用劇場作為對抗現實的方式,凝聚力量面對現況。」

保羅在《卡利班》演出時與觀眾之互動──期待他們能繼續依著熱情與信念、藉由劇場打開人心!|圖片來源:Òi Nóis Aqui Traveiz臉書頁面
訪問與整理:黃馨儀、現場翻譯:Alisson Damasceno
本參訪計畫獲「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與「台北市文化局」補助。
【1】阿利那劇團(Teatro de Arena de São Paulo,1955-1977),可謂巴西小劇場運動的龍頭老大。1950至1970年代是巴西小劇場最蓬勃發展的時期。波瓦自美國返回巴西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該團擔任藝術總監。從1956年起,以本土化為依歸,他將阿利那劇團的成就推向顛峰,並推出經典代表,首齣巴西本土音樂劇《阿利那說孫比》(Arena conta Zumbi,1965)。註釋參考自謝如欣:〈波瓦的戲劇政治化──從「被壓迫者劇場」到「立法劇場」〉,《台南大學戲劇教育與劇場研究期刊》,2014年3月第五期。頁29。
【2】相關人物解釋,請參考筆者此系列前文。
其他文章
文章回覆:
奶糖 外送茶line外約5280366和TG喝茶nini9595現金消費不喜可退換保證安全健康高中生在校生大學生模特空姐護士網路紅人可箹官網 http://www.5280344.com 本土看照選妃 https://t.me/m5280344 外流自拍情色 https://t.me/id5280344 有空來喝杯茶嗎? 台灣青茶、風味熟茶、純情好茶、火辣熱茶...應有盡有!排解寂寞、舒緩壓力,讓奶糖為你沏杯好茶TG搜索nini9595瀨5280366 奶糖外送官網 http://www.5280344.com 本土看照選妃 https://t.me/m5280344 外流自拍情色 https://t.me/id5280344 福利閒聊簽到 https://t.me/iline5280344 新手喝茶必看 https://t.me/cha05616 真實客評售後 https://t.me/mline043886 奶糖免費貼圖 https://t.me/nt5280344 成年人需要舒壓 喝茶 外約 約妹 打炮 TG搜索nini9595即享1000-5000折扣 短期兼差 一律現金消費不喜可退換 純台正妹 全台灣可約 保證安全健康 台灣幼女蘿莉高中生在校生大學生可箹 熟女人妻模特JKF女郎空姐網路紅人兼差 #北部高級尤物高檔妹TG搜索nini9595 *長榮現役空姐麻豆身材巨乳長腿 *雨非 165/47/26歲/E奶 *20000一節 四節54000 *淡江校花級別尤物蘿莉可愛 *小雅 155/45/19歲/D奶 *18000一節 四節36000 *JKF女郎傲人身材巨乳高挑 *彬彬 168/49/24歲/G奶 *20000一節 兩節36000 四節54000 #中部高級尤物高檔妹瀨5280366 *清水高中校花蘿莉幼齒正妹 *恩心 155/45/18歲/E奶 *16000一節 兩節32000 *台灣+日本混血兒 爆乳小模 *桃子 165/47/23/E奶 *25000一節 兩節40000 #南部高級尤物高檔妹TG搜索nini9595 *北部莊敬學生妹高顏值幼齒可愛 *可心 155/45/18歲/C奶 *15000一節 兩節24000 三節30000 *俄羅斯混血尤物高挑大奶蜜桃臀 *安心 165/48/24歲/E奶 *30000一節 兩節44000 上面的妹妹都是奶糖自己私藏的只會推薦給VIP客戶約 不管是身材、外貌、還是服務都是的超讚高檔~一定給你不一樣的體驗~ 最近可接新客~歡迎各位大佬來品嘗~